【哲學的重大辯論 Ep. 9】Nietzsche vs. Heidegger on “The Will to Power” vs. “Meditative Think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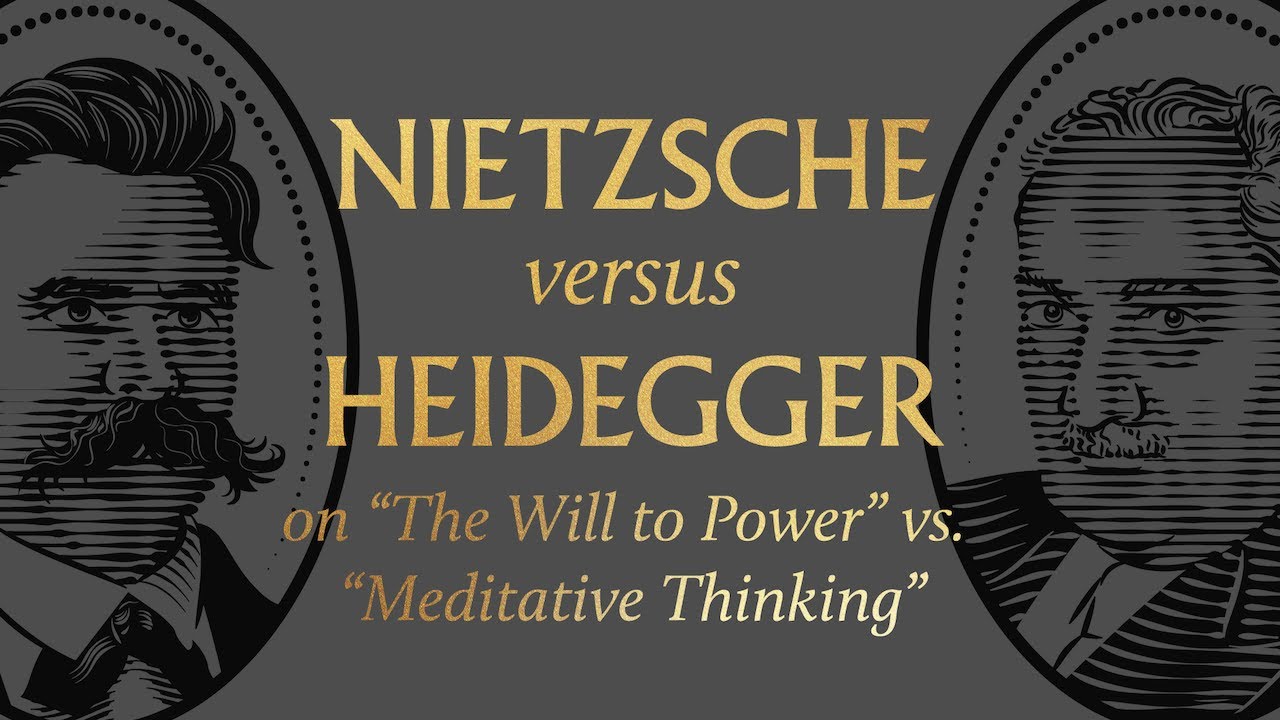
簡介
In lecture 9, Dr. Kreeft discusses Nietzsche, whose views on truth and meaning created something of a catastrophe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Heidegger tried to dig his way out of the ruins created by Nietzsche by appealing to what he called Sein—“Being itself.”
在第九堂課中,克里夫博士(Dr. Kreeft)討論了尼采,他的真理和意義觀在哲學史上製造了一場災難。海德格爾試圖從尼采創造的廢墟中挖掘出路,方法是訴諸他所謂的「存在本身」(Being itself)——「Sein」。
頻道Word on Fire Institute - www.youtube.com/chan...
Youtube影片列表連結 - youtube.com/playlist...
Youtube影片連結 - youtu.be/7X0heCzy10E...
影片官網 - www.wordonfire.org/v...
影片
全部內容
第九講是尼采與海德格爾對「權力意志」與「沉思性思考」的辯論。
凱爾凱戈爾(Søren Kierkegaard)和尼采通常被視為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的雙創始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正確的,但從另一種意義上說,這是完全錯誤的。
從三個方面來看,這確實是正確的。首先,他們都將哲學視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存在的方式,而不僅僅是思考。他們關注的焦點是具體的個人人類存在,而不是抽象的普遍本質。其次,他們具有相似的人格特質:古怪、不守常規、有爭議、被誤解,最重要的是,充滿激情。他們都是非黑即白的哲學家。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都是深沉的宗教信徒,即使尼采是一個無神論者,事實上,他是有史以來最徹底的無神論者,因為對尼采來說,無神論本身就是一種宗教。
第三,他們都有共同的敵人:現代人(modern man),向《Brave New World》邁進了一半,缺乏激情,隨波逐流,老底嘉人(Laodicean),溫不冷熱(lukewarm),沒有凱爾凱戈爾所說的無限激情,也沒有尼采所說的狄奧尼索斯(Dionysian)精神。如果他們兩人見面,我認為他們會理解彼此,儘管他們不會理解對方的哲學。第四,他們都將蘇格拉底和耶穌視為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兩位兩位人物,他們是西方文明繞著運轉的雙星。
然而,將凱爾凱戈爾和尼采稱為雙胞胎也是完全錯誤的,這有三個原因。首先,他們對蘇格拉底和耶穌的看法截然相反,尼采將他們視為兩個惡棍。他反對蘇格拉底的程度幾乎與反對耶穌一樣大,而凱爾凱戈爾將他們視為兩個英雄。第二,他們在人類生活中最重要的分歧問題上完全意見不合。凱爾凱戈爾說,他寫的一切都只關乎一件事:如何成為一個基督徒,不僅在思想上,更在人格上。而尼采則看到了和體驗了無神論的後果,他著名地稱之為「上帝之死」,並完全地生活在這種狀態中,就像凱爾凱戈爾生活在他所反對的狀態中一樣。
第三,他們在倫理學或道德學問題上也存在著根本的不同。尼采提倡教導所謂的「所有價值的轉化」(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並攻擊所有基督教價值觀,認為它們去人性化、否認生命和軟弱。
讓我們來看一些道德差異的例子:首先是無私、仁慈、慈善、愛、友善、同情心、憐憫、寬恕和促成和平。尼采討厭它們所有。他美化戰爭和殘忍和暴力。憐憫在他看來是最大的罪惡。他目睹一匹馬在街上受到毆打而產生的憐憫之情,引發了尼采的瘋狂,使他最後十年生活在精神病院。
第二是正義、平等、民主和普通人類價值。對尼采來說,人類只不過是超人(superman)、超我(overman)或新人類(new man)的尷尬存在,這個新人類沒有良心,沒有上帝。
第三是對世界的冷漠和對另一個世界、靈魂、精神、永恆和提供這些神話和分心的上帝的信仰、希望和愛。
第四甚至是誠實或追求真理的意志。
尼采是第一個提出他所謂「最危險的問題」的哲學家:「為什麼是真理?為什麼不是虛假(untruth)?」這是一個用頭腦至少是無法回答的問題,因為所有頭腦的主張都是對真理的主張。它只能用意志、用心靈,用卡爾·倫德(Karl Rönder)所謂的「基本選擇」來回答,這是一個在光與黑暗之間的選擇。
基督在約翰福音3:19中基本上說了同樣的話:「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This is the condemnation, that Light is come into the world, and men love darkness rather than light.)
這可能是無法原諒的對抗聖靈之罪的含義。
對尼采來說,真理只是另一個名字的神,一個沒有面孔的神。事實上,我認為,凱爾凱戈爾會深刻地同意這種認同,因為他相信說過「我是真理」的人是上帝——尼采所說的「難以忍受」的上帝,因為他知道所有真理,包括尼采自己黑暗的一面。
尼采最終的價值觀不是真理或追求真理的意志,而是權力和權力意志,他稱之為「存在最內在的本質」(the innermost essence of being)。
對尼采來說,權力不是中立的手段,而是最終的目標。基督放棄的權力,魔鬼在荒野的三個誘惑中提供的權力,是尼采的上帝。
尼采在故意稱自己為「敵基督」(Antichrist)時,並不是開玩笑或誇張。
尼采認為道德的起源是猶太人的聰明計謀,旨在剝奪獅子(異教徒,他們是天生比猶太人優越)的爪子,發明了罪惡感,並提出了一個真實、客觀、普遍的道德法則的概念,從而將所有人降到同一水平,即猶太人的水平。尼采並不是像納粹那樣的生物種族主義者,但他確實將發明道德和宗教的責任歸咎於猶太人,並更強烈地將責任歸咎於基督徒,因為他們加劇了這種情況。他稱基督教是所有可想像的腐敗中最偉大的,是所有扭曲之最,是迄今為止存在過的最致命、最誘人的謊言,是文明所帶來最令人厭惡的退化形式,是人類內在最嚴重的扭曲,是人類唯一無法撲滅的惡名。
這是一種比希特勒更深層次、更充滿激情的反猶太主義和反基督教,因為它是一種精神上的反猶太主義,而不僅僅是生物上的。在尼采看來,猶太人要為他所謂的道德家譜學,即道德的謊言的起源負責。他教導我們必須超越善惡本身,成為超我,不是朝著更美好的善邁進,而是超越道德善惡的本質,超越二元性,超越善與惡以及善的意志之間的區別,正如他同樣說過,我們必須超越真理與虛假,或光與黑暗,以及真理的意志,他希望克服這一點。
我們必須擁抱他所謂的權力意志,而不是真理的意志或善的意志。這就是所有撒旦教邪教的根本動機。
尼采認為道德罪惡感使人變得無脊樑和軟弱。哈姆雷特在他的著名獨白中暗示了這一尼采主義思想,當他說道:「意識使我們所有人都成為懦夫。」對於宗教來說,聖人是英雄;對於尼采來說,聖人是懦夫。
多斯托耶夫斯基向我們展示了試圖通過殺死良心成為超人的尼采式角色的難忘肖像。在《罪與罰》中,拉先尼科夫和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伊萬·卡拉馬佐夫,結果並不是尼采理想化的征服所帶來的勝利異教喜悅,而是瘋狂,在這兩個文學人物和尼采自己身上都是如此。良心沒有死,它報了仇。尼采在精神病院的最後幾封信中簽名,稱為「被釘十字架者」。
與今天的淺薄和舒適的無神論者不同,尼采看到了上帝之死的必然後果。瘋子宣布上帝之死的預言布道是世界文學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段落之一。尼采寫道:「上帝去哪了?我將告訴你。我們殺死了他——你和我。我們都是他的兇手。但我們是如何做到的?我們是如何喝乾大海?誰給了我們海綿來擦乾整個地平線?當我們解開這地球與太陽的鎖鏈時,我們做了什麼?它現在在哪裡?我們現在在哪裡?遠離所有太陽?我們不是永遠在墜落嗎?向後、向側、向前,向所有方向?有沒有上下左右?我們不是在無限的虛無中漫遊嗎?我們不感覺到空虛的氣息嗎?它沒有變得更冷嗎?夜不是越來越多地降臨嗎?」
「上帝已死。上帝仍將死亡。我們殺死了他。我們,所有殺手中的殺手,如何安慰自己?……這偉大的行為是否太偉大而超出了我們的能力?我們一定要成為神,才能讓這行為顯得值得嗎?世上從未有一種比這更偉大的行為,而任何在這之後出生的人,因為這個行為,他將成為比所有歷史都更高的歷史的一部分。」
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也看到了無神論的不舒服後果,他用尼采式的洞察力和預言,但沒有尼采式的詩意,寫道:「上帝不存在,我們必須面對所有後果。存在主義者強烈反對一種世俗道德主義,那種主義希望以最少的代價廢除上帝。像這樣:上帝是一個無用的昂貴假設;我們正在拋棄它;但同時,為了有倫理、社會和文明,必須認真對待某些價值,並認為它們具有先驗性的存在。必須認為誠實、不說謊、不打老婆、生孩子等是義務,具有先驗性的存在。所以我們將嘗試一種小技巧,使我們能夠證明價值仍然存在,即使上帝不存在,我們將找到誠實、進步和人性主義的同一規範,我們將使上帝成為一個過時的假設,它將平靜地自行消亡。相反,存在主義者發現上帝不存在的事實非常令人不安,因為所有找到價值的可能性……都隨著祂消失了;不再有先驗性的善,因為沒有無限和完美的意識來思考它……因為事實是,我們處於只有人類的平面上。多斯托耶夫斯基說過:「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以的。」這正是存在主義的起點。確實,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以的,結果人類就變得孤苦無依(forlorn)了。」
海德格爾試圖從尼采式災難的廢墟中挖掘出路。他像尼采和薩特一樣,也是一位無神論者。他絕對不相信猶太-基督教的上帝。但與尼采和薩特不同,他相信有先驗性的東西,有絕對的東西。他稱其為「Sein」或「存在」(being),即「存在本身」(being itself)。他將其與「Zayin desu」(存在、實體、客體(beings, entities, objects))和「Dazain」(存在、在場、意識和關懷、人類主觀性、存在的意識(being there, or being present, or consciousness and care, human subjectivity, awareness of being))區分開來。
培根(Bacon)在人類和自然之間提出了一種二元論。笛卡爾(Descartes)在心靈和物質、心靈和身體之間提出了一種二元論。薩特(Sartre)在「自身存在」(人類主觀性)和「存在自身」(人類主觀性的客體,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之間提出了一種二元論。但對薩特來說,就像對尼采一樣,沒有存在,沒有存在本身,沒有絕對的東西來協調和解釋相對的東西,沒有二元背後的統一性。
對海德格爾來說,存在是實在的。事實上,存在是海德格爾唯一的追求,他唯一的問題。他描述他的思考是:「將自己局限於一個想法,那一天像世界天空中的星星一樣靜止不動。」這是海德格爾對尼采的回答。
「存在之存在是什麼?為什麼有存在,而不是無?」(What is the being of beings? Why are there beings at all rather than nothing?)他寫道。「這就是問題。」「存在之存在是什麼?」
我們提到的一切都是,但如果我們想抓住存在,那總是好像我們在向虛無伸手。所以尼采似乎完全正確,當他把像「存在」這樣的最高概念稱為蒸發的現實的最後一絲,存在錯誤。尼采說的是真話,還是他自己只是長期以來錯誤和忽視的最後受害者?如果人類,即使在他們最大的陰謀和成就中,仍然與存在有關係,但很久以前就掉進了無知的存在中,這會怎樣?而這是否是他們衰落最內在和最深層的原因?
現在,如果我們用「上帝」一詞代替「存在」一詞,這就成為了一種深刻的診斷。這就是像Sajanitsyn這樣的先知所做的事情,但用海德格爾所做的「存在」一詞代替「上帝」一詞,就成為薩特所批評的舒適的人本主義(humanism)。這就像用「道德」、「責任」、「民主」、「包容性和多樣性」(inclusivity and diversity)或「社區」等舒適而無牙的抽象概念來代替有生命的上帝。
然而,海德格爾可以提供幫助,並向我們展示一些真正的洞察力,如果我們去看的話。他說有三個通往存在的道路。第一個也是最自然的道路是通過存在。這是古典的道路。首先,看看事物,然後問它們共同的存在是什麼,使它們成為現實。這引導我們走向上帝,所有存在的來源。
第二種方法,現代方法,是從Dasein(存在)、意識、主觀存在開始,即你在自己身上發現的東西。海德格爾在他的第一本最著名著作《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中試圖繪製這條道路,但留下了未完成,並承認它是一個失敗,儘管它探索了Dasein或意識的存在,並提供了許多深刻的心理洞察力,例如我們每一個時刻的存在從一開始就是向死亡的存在。
海德格爾在他的後期著作中轉向了第三種方法,這是一種直接的、神秘的或詩意的方法。這種轉變非常劇烈,學者們經常談到海德格爾1和海德格爾2。海德格爾2像詩人一樣折磨、拉伸和玩弄語言,一些學者讚揚這是一種無可比擬的深刻,而另一些人則說這是怪物和無意義的假冒。
海德格爾的所有著作中都清楚地表明,需要一種與計算或科學思考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由於這一點相當清楚,相當實用,且不依賴於理解海德格爾臭名昭著的困難哲學的其餘部分,因此我們有義務仔細研究這種思想。最簡單的來源是海德格爾在名為《思考的對話》的短對話開頭所做的紀念演講,可以找到德國標題為「Gelassenheit」的演講,字面意思是「釋放」或「冷靜」。
海德格爾希望描述一種與我們越來越熟悉和越來越擅長科學和技術思考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他描述這種思考方式為:「當我們計劃、研究和組織時,我們總是計算已知的條件。我們以計算的故意將它們考慮在內,使它們為特定的目的服務(這句不懂怎譯,We take them into account with the calculated intention of their serving specific purposes)。因此,我們可以依靠確定的結果。」
這就是我們的技術如此成功的理由。計算思考是計算的(It is calculative thinking that computes)。海德格爾在計算機革命之前寫下了這句話,但這是預言性的。相反,海德格爾呼籲一種需要努力、耐心和關懷的沉思性思考,就像植物而不是機器一樣,但它是任何人都能開放的,因為它是人類本性中的力量。但我們正在忽視它。我們越來越多地生活在我們自己的創造和媒體的人工世界中。海德格爾在1944年寫下了這句話,而今天這句話比當時更真實。如果海德格爾今天還活著,他會說我們正在生活在《黑客帝國》(The Matrix)中,更喜歡虛擬現實,而不是有真實存在的存在。他稱之為一個不是世界的世界的幻象。
海德格爾預言性地預測,我們可以並且將把我們自己的本性變成一個優越的機器;我們通過征服人類本性,把它變成生物和化學上的超人,而不是尼采的精神超人,來完成我們對自然的科學和技術征服。海德格爾寫道:「當生命被交給化學家時,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合成、分裂和改變生命物質,這時候就快到了。」他寫這句話時,離基因組項目掌握整個基因密碼還有許多十年。
他寫道:「一場用技術手段對人類本身的生命和自然進行的攻擊正在被準備,氫彈爆炸與之相比只是小事一件。」他的解決方案不是魯德派(Luddite)的退縮,因為他說:「現代技術決定了人類與所有存在的關係。它統治著整個地球。它會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前進,而且永遠無法停止。這些力量早已超出了人類的意志,並超過了他們的決策能力。」
如果這句話是真的,海德格爾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它由兩個部分組成:他所謂的「釋放事物」(releasement toward things)或「技術的冷靜」(detachment toward technology),以及對神秘的開放。第一部分並不清楚,但神秘。第二部分並不神秘,但清楚。神秘就是存在本身。對存在本身的開放不是被積極描述的,而是負面描述,即不計算、沒有意志地思考,放棄尼采的權力意志,回歸真理的意志,不僅是關於事物的真理,甚至不僅僅是關於我們自己的真理,而是關於存在的真理。
釋放意味著冷靜,從我們自己的技術冷靜,與所有聖人教導從一切小於上帝,小於存在的事物冷靜平行。這包括從我們自己、我們自己的意志和我們自己的清晰、計算、成功的思考類型冷靜。
即使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並使用它,我們也可以從這個世界冷靜下來。我們也可以對我們自己的技術做同樣的事情。
海德格爾寫道:「我們可以使用技術設備,但同時保持自己如此自由,以至於我們可以隨時讓它們去。」這是否天真?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觀察今天的青少年如何輕鬆地使用智能手機。海德格爾並不天真。他比我們大多數人更清楚危險。
什麼危險?C.S. Lewis所謂的「人類的廢除」。不是身體上,而是精神上。對路易斯來說,這意味著道德良心的死亡;對海德格爾來說,這意味著沉思性思考的死亡。
海德格爾寫道:「人類處在危險的境地。」為什麼?因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會導致人類的完全滅絕和地球的毀滅?不。在這個原子時代的黎明,一個更大的危險威脅著,即技術革命可能會如此迷惑、迷住、閃耀和引誘人類,以至於計算性思考有一天可能會被接受和實踐為唯一思考的方式。問題是拯救人類的本質。索倫的戒指(《魔戒》)存在。我們會成為戈勒姆(Gollum)、失去我們的本質,還是成為弗羅多(Frodo),拯救它?海德格爾不是神學家,但他仍然可能是一位先知,雖然是一位黑暗的先知。
我們已經將尼采與凱爾凱戈爾、海德格爾、蘇格拉底和耶穌聯繫起來。現在讓我們在對話中添加第五個名字。阿道夫·希特勒。尼采和海德格爾與希特勒也有非常發人深省的關係。令人震驚的是,像海德格爾這樣深刻而敏感的哲學家加入了納粹黨,沒有抗議希特勒開除他的教授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現象學(phenomenology)的創始人,一位偉大的哲學家,僅僅因為他是猶太人,海德格爾還接管了胡塞爾的職位,並寫下了以下關於希特勒的言論。這是海德格爾的話。
「國家社會主義革命不僅是一個黨從另一個黨手中奪取國家權力的問題,而是帶來了我們德國存在的完全革命。學說和思想將不再統治你的存在。通過我們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整個德國現實已經改變,這意味著改變我們所有先前的想法和思考。知識和學問的詞語已經有了不同的含義。現在,一場激烈的戰鬥將在國家社會主義的精神中打響,這場戰鬥必須扼殺仍然束縛我們的人文主義基督教觀念。1933年5月10日公開焚燒猶太馬列主義著作的行為象徵了這場鬥爭。德國人,加入這場鬥爭。讓你的參與公開化。從出版商和書店,把所有值得焚燒的書籍和著作送給我們。」
有沒有偉大的哲學家寫過比這更反哲學的東西?海德格爾哲學的深刻與納粹熱情之間的鮮明對比幾乎令人難以置信。這令人驚訝的對比教導我們什麼?它只是表明深刻的哲學家可以政治天真?這不僅僅是可怕的政治;這也是可怕的哲學。這是否意味著海德格爾只是一個假貨,根本不是深刻的哲學家?這太簡單了,也忽視了數據的另一半。這是否意味著僅僅深刻的哲學無法拯救我們免於道德愚蠢甚至瘋狂?好吧,是的,但我們在遇見尼采時已經學到了這一點。這是否意味著當一個人停止崇拜真神,他就會被誘惑去崇拜一個非常黑暗的假神。當上帝死亡時,人性中的上帝形象也會死亡。是的,但我們在閱讀《舊約》時已經學到了這一點。這是否意味著我們現在生活在上帝死亡和人類死亡之間的短暫時間?唉,我恐怕這可能是海德格爾和尼采都教導我們的教訓。
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一個絕對不是哲學家的人,欽佩尼采,墨索里尼也是如此,他實際寫了一些哲學,為納粹主義辯護,將其視為道德相對論的邏輯結果。尼采雖然是德國人,但既討厭德國人也討厭猶太人,他不是種族主義者,也沒有像希特勒那樣將政治放在中心地位。但尼采不會對納粹的暴力、權力意志和軍國主義感到震驚。他寫了許多納粹方便利用的東西,尤其是他對戰爭、暴力、精英主義的讚美,以及他對平等、同情和基督教愛的輕視。尼采和希特勒都教導回歸基督教前的異教道德,這就是抹去人類歷史基本教訓。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