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書作家分享精華|李智良:如果寫作不是一個表演,它最後就是通往人軟弱和溫柔的部分

主持:首先請你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李智良:我是李智良,香港作家,雖然稱為「作家」但出版的書只有幾本,其中《房間》因為探討精神病的議題,比較多人注意。除了寫作之外,我之前在大學教寫作課、香港文學和電影欣賞的課程。最近這一兩年,我去了加拿大讀書,也是修讀寫作的藝術碩士(MFA)課程,很感謝 Dobby 和 Matters 的朋友邀請我來參加這個分享。
寫作的源起
主持:能否談談你的寫作與出版歷程?起初進入寫作領域時,對出版與刊物的思考,到了後來,有沒有什麼變化?
李智良:我小時候已有寫東西,就像很多朋友都會寫日記,我以前有本很漂亮的日記簿,有一個鎖,但寫到中學,發生了件「災難事件」,有天發現日記被人打開過,之後便覺得,不可以寫自己、不可以坦露自己的所有想法。不寫日記,但仍有表達的慾望,寫作是一種自己和自己的對話和陪伴。後來中學時嘗試寫短篇小說,那時純粹想和朋友分享,在原稿紙抄寫得很漂亮,然後影印送給朋友。那個時候算比較有意識在「寫作」,除了自己看,還會和人分享。到90年代中上大學的時候,有很多雜誌、報紙副刊,有些欄目是給完全沒有人認識的作者和年輕人去投稿的。我那時讀比較文學,喜歡文學、電影,便寫些隨筆、小說之類的東西。當時有朋友在《快報》一版叫《Young Express》的副刊做編輯,便邀我寫些隨筆、電影筆記。
另外一個背景是,我是透過閱讀對寫作產生興趣的。小時候有段時間經常搬家和轉校,讀過三間中學,住過不同的地區。以前80、90年代沒有這麼多的通訊工具,搬家轉校就跟大部份朋友失聯,很多時就要是要自己陪伴自己,便去了圖書館。有一段時間在新界上水,在那個很小的公立圖書館,書架上有一排台灣志文出版社的書,翻譯了許多世界文學著作,便開始對「文學」感興趣,所以我沒有看過金庸,或者比較多人看的亦舒之類的作者,反而是看一些看不明白的書,但是覺得很吸引。
第一本作品《白瓷》的自資出版經驗
李智良:到後來,出版第一本書《白瓷》是1999、2000年之間,那時除了有中文寫作也有寫英文,都是寫些像詩的東西,或是很短的故事。那本書是自資出版的。那時有位老師,我忘了是借錢還是當作是一份禮物,送了幾千元給我,朋友也一人夾幾百元,我自己又儲了些錢,湊夠出版的資金。我其實對出版流程一點都不懂,以前的出版流程複雜一點,和現在電腦排版很不同。當時有家二樓書店叫「尋書店」,書店老闆和職員都是朋友,便由他們幫忙排版、對稿。真正出版製作的,是我和我的弟弟漫畫家智海,他幫忙改稿和設計封面。最麻煩是印了1500本書,因為沒有倉庫,全部書送到我家裡,那時我們住在很小的公屋單位,十多廿箱書塞在床下、堆疊在家中一角。那1500本書賣了十幾年,才叫做賣完。其實很多書是自己去找地方寄賣,很多時出了貨但錢卻收不回,但這個經驗令到我對出版,由生產到最後的銷售,在產業線上看到了整個過程。
第二本作品《房間》的起源
主持:《房間》的口碑很不錯,主題深刻,相隔多年,上月資深藝術家楊秀卓仍提到參考了《房間》作為他的藝術展覽的靈感,對於成書的過程、出了第一本書之後的路徑,你有什麼想分享的?
李智良:然後談2008年出版的《房間》。2000年因為社會運動的關係,有段時間開始比較留意香港的社運,認識了「自治八樓」、「獨立媒體」的朋友,印象中從2000年到2010年這段時間,文藝圈和社運圈的人有很多交疊。另一個背景就是 Web 2.0 興起,要建立一個Blog(網誌)很容易:既是私密的個人的空間,同時又像在有公共性的小群體裡面。那時候開始在網誌寫自說自話的東西,也有寫一些香港社會現象的評論。
後來因為精神科治療的壞經歷,開始去找除了精神科以外,如何理解自己狀態的資源,於是也開始在網站多寫這個課題,還有就著所謂「精神病患」和城市生活的壓抑,又多寫。《房間》的出版,是將網誌裡的文章重新編輯一次,那時請到《字花》的一位編輯郭詩詠幫我看稿和編輯,也找了出版小團體「廿九几」(一個成員當時都是二三十歲的藝文出版的組織),也找了獨立書店/出版社Kubrick合作,很DIY地去做這件事。之後因為《房間》,開始有文學圈的前輩與大學老師認識到我,邀請我去兼職教寫作、香港文學和電影相關的課程。從此,我開始對自己是一名「作家」這個身份多了自覺。但是身為作家這個意識反而令到自己更焦慮,每次要發表文章都會和自己的名字掛上,就會很大壓力。其實《房間》之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我都寫得很慢,也有不知道自己想寫些什麼。
因為那些人認識你,是因為精神病的議題,但那個不是我的全部。即使到了今天,很多人還是拿著《房間》跟我說:「很喜歡這本書」,但很少人會提起之後出的書,其實那些才是我最想做的創作。
《房間》的出版是一個行動
主持:雖然你說許多人只會提《房間》,但我可不可以問這本書呢?就是你在《房間》裏面寫精神病患的議題,一件如此私人的事情,在你書寫的出版的時候,你有沒有想過它會變成了公共的一部分?
李智良:現在回想,出版《房間》是一個行動。當時跟朋友談,都是有類似想法。在2000年到2010年那段時期,我們那一輩「70後, 80 後」的人很相信公共討論,個人和政治是充滿交集和聯繫的。會有這些想法就是覺得,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我做很多資料搜集的時候,看到在我身上的經歷,和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人身上發生的都很相似,因為它有一個共同的結構:藥廠和精神科的產業問題。有了這樣的視野,便覺得我的故事不只是我的故事,我的出版也不只是為了我自己的出版,而是一種資源分享和一種現身。其實到了今天,凡是講「精神病」的問題,都是由專家來講,包括社工、臨床心理醫生、精神科醫生、政策的決定者;又或者是新聞評論,也總是像評論一宗悲劇。甚少是由那位「被判病」的「精神病人」現身說法,將他的經歷放回注視的中心。從他出發的經驗,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那時候出了這本書迴響不少,很多人都經歷過類似的處境,家人、朋友甚或自己都接受過精神科治療。他們讀這本書有很多共鳴,也得到某種安慰或者支持。
從《房間》的公共連結到《渡日若渡海》的疏離
主持:我看《渡日若渡海》的時候,覺得有一種疏離、陌生、孤獨的感覺,但聽你說,你認識社會運動的人,關注社會事務,這一方面又很公共、很有連結。在這個位置中間,應該不算是矛盾,但是中間那條線,你怎麼去看?
李智良:多謝你這個問題!感覺被撃中了,這實在是我很困惑、想不出答案的問題。我的生活經常都有孤獨感,也都因為這樣,有對連結社群的渴望。我不知道這樣講會不會太嚴重,可能我的書寫,就是嘗試去回應這種慾望。當我極力去寫很漂泊、孤零的經驗時,其實它是一個邀請,希望其他人都看到自己,這些類似的經驗,可不可以互相關聯?我覺得就算寫所謂虛構的作品,背後都有對於世界結構、對社會的判斷,只是我寫不到那些很有愛、很溫暖的故事。
生活是碎片,有12年寫不出東西來
主持:你在2008年寫完《房間》之後,你說你有十多年不是很寫到東西 ,到了下一本書,已相隔了12年。我們今天來聽的觀眾,可能都會想知道怎樣持續寫作。但現實是,其實未必可以持續寫作的,不是真的那麼順利,對於你來說,中間這12年你的想法怎樣?
李智良:1999年出版《白瓷》的時候,有朋友問我,下一本什麼時候出版?我說應該不會那麼快,怎料要拖到2008年,拖了9年。第一本和第二本之間拖了9年,第二本和第三本之間是12年,連那位朋友都過世了。
兩本書之間的時間,我找不到很暢順的寫作狀態,有些人可能很有紀律,或者可以給自己比較安定的生活節奏,創造持續寫作的空間,但我一直在這方面都有些吃力。這和自己的私人生活狀態有關,有很長的時間,我都沒有一個很穩定的居所,無論和家人住、還是自己住,都是不停搬屋。我和弟弟數過,單在香港就搬過20多次屋。另外,我從來都沒有做過全職工作,沒有穩定的收入,就算後來兼職教書比較穩定一點,都是零散工作,每個學期只有那十多個星期按時數計薪,暑假、寒假、備課的時間都沒有薪水,每個學期都要重新簽約,隨時會中斷,可以說是有點「朝夕不保」的狀態。當然不是說沒有地方睡、下頓飯沒有錢付那種,但是這個學期跟下個學期會不會有工作,可以教甚麼學科,都由不得自己控制,其他自由工作的邀請也是,你推一次、再推第二次,別人就不會找你第三次了。
所以有時候會很焦慮,我究竟要接多少工作、才可以保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呢?但你要去接這些 make to order (制定式)的工作時,投入是挺多的。能接回來的稿題,或是教學工作,和自己想專注創作的主題未必有任何關係,工作上的投入或是跟別人的交流,也未必能滋養或幫助你的創作。
當經常要在這種不停轉換節奏的狀態中生活,便沒法營造空間給自己寫作。所以我寫的東西全部都是碎裂的,它建立不到一個很完整的世界,因為我的生活經驗就是這樣,全部都是碎裂的片段。我對時間、對感官很hyperconscious(高度敏感),這可能與生活在香港的城市經驗有關,或是「流動的現代性」( Liquid Modernity )下根本的基調如此。這種碎裂、不連貫可以說是一個缺陷、不完美的東西,但我將這種不完美當做一個方法,嘗試了比較實驗的寫作,將這些碎片呈現的不同時間點,形成如 collage(拼貼畫)一樣,或是多重曝光的影像,堆疊在一起寫。
最懷疑自己的時刻
主持:可不可以分享一個在創作的期間,最低沉的時刻呢?就是起起伏伏當中,最低沉、最懷疑自己的時刻。
李智良:我對自己很多懷疑,有些作者會有一個很強的想法、意象,他能一往無前投入去創造那個世界。我寫《房間》或之前比較接近這種狀態,或是由情緒帶動,我對某件事感覺很憤怒,或者心中有一個畫面,我就可以開始寫了。但是越寫下去,我對究竟什麼是寫作、寫作究竟是為了什麼有很多自覺的時候,就會鑽牛角尖想很多,於是癱瘓了自己。
究竟文學是不是一種表演呢?那是個很大的質疑。當然我讀很多作品都很感動,無論是它的形式、內容、作者想傳達的情感等等都直接憾動到我,但也會懷疑,那些東西你關上門如砌模型一樣自己做也可以,為什麼要印幾千本書,去跟別人說呢?剛才你問的問題很切中,就是如果我那麼渴望連結,為什麼我寫的東西又是這麼孤離的呢?
有些藝術家會幾個人共同創作,但我沒遇到這樣的朋友跟我一起做。我有時帶寫作工作坊,大家來的時候就很開心,說一定要繼續敘會一起分享創作,結果都是沒有下文。那種對於跟別人連結、交流,對社群的慾望,跟你去到真的寫作,卻是很孤獨的狀態,長期處於這種懷疑糾結的狀態,便變成寫作的障礙。但是這兩、三年,我開始會想,怎能擺脫這一大塊沒有答案的思考呢?就是寫作是為了陪自己,在過程中,其實是沉默地去觀看,沉默地去靠近一些你想理解的事情或者人,之後出來的那個作品,只是一個過程的印記。我慢慢這樣去想時,就比較鬆動了。
對於要表現給人看我做到什麼,現在會少了焦慮。書出過了,有些獎也拿過了,有些比較大的藝術家駐留也去過了。其實履歷表多一行、少一行,不會很大分別。另外就是疫情的時候,情況真的最差,一來因為社會事件,二來是疫情和人隔絕,好像自己在一個洞穴裏面,不停接收世界發生的事情,還有外來的噪音和刺激,處於很癱瘓無力的狀態,卻沒有辦法用行動、生活的實踐回應它,同時完全失語的一種狀態。
最近做的項目:有關記憶的失卻
主持:能否談談你最近做的計劃?
李智良:我最近的寫作計劃,是寫一些 2019 以後的事情(註:2019 指香港反修例運動),是與不同人的記憶有關的,你可以說主題是「記憶的失卻」。我們現在5年或1年前的事,很多東西都不會記得。為了這個寫作計劃,我去讀很多人的寫作、記錄,無論是記者、素人、朋友的記錄,來自社交媒體、記錄片、小型出版物、他們聽的歌、他們記得的畫面等等。我發現其實我不是在想最後要交出怎樣的作品,我的目標不是那個作品,而是想與這些人聊天,我覺得那個經驗才是最重要的。我去接近他們當時記錄的畫面、場景、心情,對我來說是一種幫我去哀悼,或者幫我去得到一些療癒的感覺。
這幾年,我自己有很多事情鑽牛角尖,想得自己很不開心。可能很多人都會有很多內疚、憤怒、哀傷,做這個寫作計劃時,要回看很多資料和畫面當然也很辛苦,但我覺得是一種陪伴自己,承認和容許自己的情感,還有嘗試在自己的寫作裏面去接近其他人留下來的痕跡與記憶。形式是很簡單的,好像 Twitter 一樣,一條貼文只有百多字,全部都是「You Remember 你記得.....」起句:你記得哪年哪月哪日,哪裏放了50粒催淚彈;你記得哪月哪日,我和哪人吃了一碗叉燒飯。把這些細碎的片段放在一起,我幻想它就像很多塊碎布縫在一起的大帳篷。
主持:我首先回應一點,剛剛我是感動的,因為在一個很大的政治創傷過後,很多人都會逃避,可能躲起來。雖然你說你在一個洞裏面,但是你做的計劃與嘗試,其實是一種勇氣,走出了那個洞,希望成為無論是別人也好、自己也好的一個「方式」。躲在洞裏有兩種說法,第一種是真的躲在裏面,封閉自己,不透過藝術或者創作去感知世界;另一種是那個人很敏感,他躲在洞裏面,但是很想和別人連結,當找到機會,就去做了。我想很多人都是封閉了自己,但是創作和藝術的力量就是這樣,經常都能在苦困的時刻,去找到共鳴和連結。
李智良:同意。其實我們的人生都在回應那個創傷和那段經歷。我覺得要在悲情裡面 loop(重複)下去是很容易的,我其實更想找回那些有閃光的部分。我們現在記得整件事有很多暴力、很多壓抑的情景,但其實當時並不知道未來是會怎樣發展的,我們現在以回溯的眼光,才會覺得它是一直向前,然後撞牆、崩壞、死亡這樣的一個敍事。我很想找回那些很小的時刻:可能是白鴿中了催淚彈,有人用水幫牠沖眼;或者是有些人搭地鐵,不想用八達通卡(註:因為會紀錄身份及行蹤),閘機上就有人放下零錢。這些好像很小、很不重要的畫面,其實裡面有很多關懷與能量 。
華語作家處於英語世界的寫作
主持:你之前都是用中文寫作,你目前不在香港,《七日書》很多作者都是在外地,大家會談母語的課題。在轉換環境、不再用母語寫作的課題上,你有什麼想分享?
李智良:我其實沒有很焦慮。我不覺得現在在加拿大讀書,就要成為加拿大人。怎說呢,一來是溝通功能性問題,我讀的課程有一門「小說工作坊」,每星期都要依一個題目寫一篇東西,上課要逐個同學的作品一起討論。有些時候我寫香港的故事,你知道我們的生活空間很壓迫,所以會聽到隔壁屋的聲音、樓下發生的事,但北美的樓房不是這樣,他們的城市空間形式、交流的密集程度和速度感完全不同。當我寫香港背景的故事,帶有這種氛圍,老師會很驚奇,他覺得很厲害,智良你可以這樣聯想到這麼多東西,將這麼多東西壓縮地寫在一起,很有「現代感」云云。我們過往的訓練,不可以長篇大論講很多東西,你一定要很壓縮,因為我們的生活、空間也是這樣。這些時候就會覺得,其實那個所謂美學,什麼叫「好」、什麼叫成功,有很多文化、生活經驗的差異,我覺得沒有「融入」的焦慮,因為那些別人沒有的東西,更是我們值得去擁抱的東西。
更重要的是,究竟哪些才是你的觀眾/讀者?我近年看到的香港年輕作家或詩人,他們在外面發表英文作品,但看到他們的題材、語言的感覺,其實還是很「香港」的,或者是帶有一種節奏感,那種 compression(壓縮),一詞多義的相關,都是要有香港生活的經驗才看得明白的,這些題材與寫法在外國還是會找到發表渠道也得到欣賞。的確,英文不是香港大部分人的生活語言,但「國際」市場就是英文出版主導,沒有英文出版,在國際上便沒有能見度,但這也不等於你就要假裝自己不是從一個香港人的語言與生活經驗般去寫所謂「純正」的英文。
香港人經常焦慮自己英文不好,甚至覺得一定要學到好像西方人那樣的口音、句子結構、用詞。我又覺得不必,所以我不是很困擾。比較困擾的是到真正發表的時候,應該怎樣剪輯整個稿子,或者是究竟觀眾應該面向哪裏?我的心是面向跟我生活經驗比較接近的人,同時我又用英語發表的時候,究竟這兩個很不同的場域,怎樣可以有一種溝通或者互相看見?這個才是困難所在,北美也好、歐洲也好,發表場域每每就是以西方中心為主的視角,而對於「外面」或「他者」的經驗,有很多很模板的想像,你要怎樣克服那些想像,然後找到一個位置,既可以對自己心中的觀眾溝通,同時也都是讓所謂「世界」的觀眾都會覺得有關聯?我想這不只是一個作者可以解決的問題,需要很多作者、譯者、研究者、出版人一起實踐中摸索。
何時理解到「坦誠面對自己」是一種「方法」?
主持:談了差不多一個半小時,我覺得你很坦誠、很能面對自己,當然在作品裏面更深,不論是心理健康,或者是《渡日若渡海》那種自己和他人的距離,那麼的忽遠忽近,都是需要很坦誠面對自己才能寫到的。我想了解,你是什麼時候開始覺得,「坦誠面對自己」是一種「方法」?
李智良: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很坦誠,大家讀《房間》都覺得我很坦誠,但還有很多東西我都沒有寫出來。寫作始終是一個有意識的、有篩選的過程,但是可能真的和自己的成長經驗有關,小時候試過被人欺凌和孤立,也有你以為是很多年的朋友,會用其權力或者話語權公開壓制你。我覺得這些經驗很多人都有,我心裏的渴望是,會有一個人會肯定你的感受。我記得以前很抑鬱,什麼都看不到的時候,我會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如《罪與罰》、《群魔》等,我記得書中對很複雜的人、很大奸大惡的人,也寫到他們很脆弱的部分,他們也有自己光輝的部份。他的人物是很複雜的,但是他的故事能載著你,在故事的空間裡,容讓眾多的聲音走出來,例如是受損傷、受侮辱的人;變得憤怒、變得邪惡、變得冷酷的人都有。
有時候我覺得寫作,如果它不是一個表演,它最後就是通往人軟弱和溫柔的部分。你可以接通到軟弱和溫柔,其實是一件很 radical(前衛、進步)的東西。我們的社會每樣事情都講求事工、效率,講求撇除感性諸如此類,我想我寫作時,會很想讓自己進入這個比較柔軟的狀態。我寫的東西都很沒有故事性,但還是會看到人物:作為故事中的人物,究竟外層剝落了,剩下的那種軟弱、vulnerable(容易受傷的)部分,是甚麼呢? 面對著這樣的世界,他怎樣站、怎樣走?
我最初在網站上寫作,當它樹洞,但它又有些公共性。但在《房間》之後我都吃了不少虧,因為用自己的名字發表,以第一身講自己的經驗,基本上是向全世界公開病歷。但如果你再問我,我想我都會出版的。公開了自己,遇過不開心的經驗和麻煩,但是總的來說,都是好的多過壞,只是後來我就沒有再用第一身寫東西了。
給寫作者的建議
主持:如果要總結幾個要點,去給寫作者一些建議,你會如何歸納?
李智良:第一,就是為自己而寫,先寫了,是否發表之後再想。書寫是一種肌肉記憶。剛才我說很多時沒有很穩定的狀態去寫,但有些方法還是有幫助的,就算不是天天都做到,一個星期能做到一兩次也好。如果你寫日記就寫日記,如果你不想這麼赤裸,你可以寫「夢的日記」,一起床就寫,記下夢,當進入了一個打字的狀態,再由那個狀態過渡至更認真的寫作,會容易很多。
如果不寫夢,就做 Free Writing(自由寫)或者 Automatic Writing (自動書寫),拿出三至五分鐘,什麼都不想,凡經過腦海的東西就打出來,我覺得打字是有幫助的,打字好像很 mechanical(機械式)、physical(身體性的),有些人喜歡用手寫,但手寫比較容易停下來,而打字的速度可以更有 momentum(動能),比較容易進入那種自動書寫的狀態,因為身體已經進入了寫東西的狀態。
我最近聽到一位跨媒介的藝術家分享,又寫詩、又寫小說、又拍照、又拍影片、又做雕塑,她其實不會被媒介所規範。她寫的東西也是在做雕塑時在思考的,然後又將做雕塑的經驗搬到寫作之上。就是說,你動用自己寫作的各種感受、思考或者創作資源,其實是可以穿越不同的媒介。畫畫的時候不一定要用畫畫的腦,你可以用畫畫的腦去寫作、用寫作的腦去畫畫。我自己就是這樣,我對視覺和聲音很敏感,所以那些東西常常會進入寫作。
李智良推薦:喜歡的作家、有啟發性的作品
主持:能聊聊你喜歡的書、作者嗎?
李智良:
一、Clarice Lispector
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巴西猶太裔女作家,她的寫作直接影響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學者Helene Cixous對女性書寫的理論探索。
二、Bhanil Kapil
印度裔英國詩人,也有做行為藝術,在美國教書。她有時候會做 lecture performance。她寫印巴分治的歷史、南亞人在歐洲遇到的種族歧視,對精神疾病議題也有關注,但是寫得比較實驗,跨越詩/散文詩/非虛構/小說的界線,我覺得很有趣。
三、Warsan Shire
詩人,索馬里難民作家,有一首詩很出名,叫Conversation About Home,講什麼是家園。內容是在難民營裏訪問不同的人的經驗,將不同的受訪者經驗拼貼,形成好像有一個主角的故事,講他要逃離戰火的家園的經歷。
四、Marguerite Duras,Maurice Blanchot
這兩個應該已經有很多中譯本了。
五、Adania Shibli
巴勒斯坦的作者,講巴勒斯坦被以色列殖民這麼久,當中的艱難生活。但她不是寫灑狗血、很悲慘的故事,而是內斂的,但那些暴力在故事的週邊發生,影響著每個人。她有一本作品叫 Minor Detail,另一本叫 Touch。我覺得她對於巴勒斯坦的處境、那種日常生活的暴力的呈現很特別,並非直接去特寫,或者如編年史那樣去寫,而是寫那些不會是英雄的人物的日常遭遇。如《Minor Details》就是說有主角看到一宗多年前的新聞,想去那個已經被以色列抹除了痕跡的地方,去做資料搜集,中間她遇到的故事。她寫暴力場面時,不是用很感官的寫法,反而很抽離,寫了很多地景的描述,因為殖民佔領的暴力,正正在於土地和歷史的抹除。
六:George Perec
他很喜歡寫物件和列清單,會用很奇怪的準則去推動自己的創作,例如整本書不可以有個「e」字。他來自的團體Oulipo會用和數學或者科學有關的準則,用規限去觸發自己的寫作。
出版收入有限,以Patreon作為支持與同行
主持:最後,聽你說過,Patreon 對你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平台,你有什麼想跟大家說的?
李智良:剛才講的出版問題,香港也好、台灣也好,出版也是沒有錢賺可言的,一般比較合理的合約,作者能分得約10%的版稅,但也聽過有更少,或附帶其他條件的。如果一本書訂價100元,作者會分得10元。假設一本書印行1000冊,作者的版稅收入便是1萬元,可是中間花了 12 年才寫完呢。再以在香港已算銷售很好的《房間》為例,多年來先後重印了3、4次,印量合共有5、6千本。但一般文學出版,很少會重印,只會印一刷,以這樣不成比例的時間、成本和投入的心機來說,賣書實在幫不了作者的生存。
直至早幾年前開了Patreon,大約有50、60位月捐會員,每個月40、50元一杯咖啡的價錢這樣支持我。也有些朋友會選擇年訂,或者金額再多一點,是很實質地支持我的創作和生活。也是因為早幾年開了Patreon,錢沒有花,才一直儲到這筆錢出國讀書。另外,每個月我會至少拿15%訂其他人的Patreon或捐款,支持一寫港、台作家、獨立媒體等。如果大家欣賞我的寫作,或者想支持我,可以考慮一下。不付費也可以做「免費會員」,只是並非所有文章都會看到。其實我的立意不是設一個付費牆去擋住大家,而是希望能有實質的支持,繼續創作。
(完)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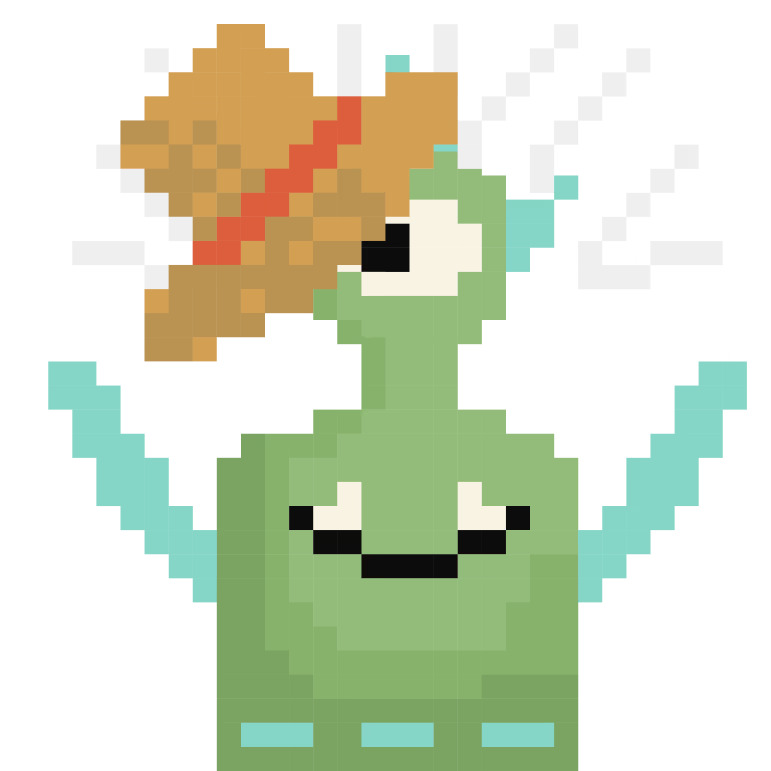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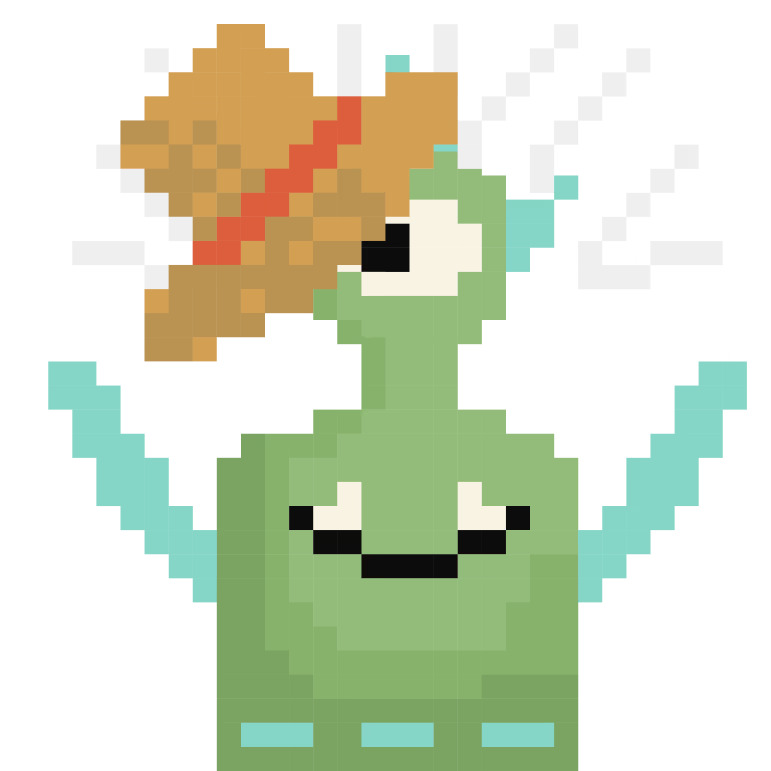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