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茸和彝族三代人的三十年
食通社说
六月,我们读书会正在共读《末日松茸》。在每周一次的线上讨论环节,来自云南的彝族返乡青年李康丽和大家分享了她和家人从事松茸采集的历史,以及对松茸贸易和消费的观察。
本文根据康丽在读书会的分享编辑而成。无论你是否读过《末日松茸》,希望本文在即将开启的松茸季之前,让你对这种蘑菇,以及围绕它的社区和产业,有更接地气的了解。
一、从北京回云南,从核桃到松茸的返乡创业
我叫李康丽,彝名依噜阿娜秀,意思是美丽的花。我家在云南楚雄永仁县中和镇小直苴村。到我家需要从楚雄坐中巴到县城,县城坐车到山下通路的地方,然后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

高二的时候因缘巧合在昆明接触到公益组织,那是我第一次接触食品安全问题,开始反思城乡差异、乡村价值,这些议题对我的思想冲击非常大,也开始了我公益启蒙。2011年,我参加了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一个人才培训计划,之后就留在了北京工作和学习。后来也开始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等平台销售核桃之类的家乡特产,还和一起做乡建的陕西男生张可结了婚。

2012年底,我鼓励老家的村民参加全国农民合作社论坛。这次北京之行让乡亲们有很多感触,开阔了视野,了解到农村发展需要大家合作起来。于是,2013年就成立了我们自己的合作社。

2015年年底,我回云南过年,就没再走,决定返乡,接手村里合作社的工作。2016年我先生也来到楚雄,和我一起推动合作社的发展,销售社员们的生态农产品,帮扶县内其他从事生态种植的小农户,一直干到现在。
我们最初只做野生核桃、野生香菇这样的传统土特产,市场接受度也很高。2013年,我们也给朋友发过一些松茸干,但以分享为主,并没有想过当成商品来卖。

2016年,有个上海的朋友拜托我给他寄一点松茸。当时的快递需要四天,松茸到上海的时候,整个都腐烂掉了。首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但到2016年底,很多人都说希望我能够分享一些当地新鲜的菌子,呼声最高的就是松茸。2017年顺丰来到我们县,我们就开始正式发卖松茸。
二、我家采松茸这三十年
虽然说直接给消费者寄松茸是这几年才开始的工作,但其实我父母从80年代末就开始上山采松茸了,卖了的钱用来支付我们兄妹的生活费和学费。

在我的记忆当中,松茸和野生菌几乎是我们这样一个在山上生活的家庭90%以上的经济来源。可以说,我是靠着卖松茸的钱才能一直读到高中毕业,成为村里汉语最流利的孩子。
90年代松茸价格最高,一公斤能卖到3000元。我妈妈说那时候她一天能采280块钱,那时这可是很多很多钱。2003年非典以后,价格好的时候也就600元左右一公斤,差的时候可能两三百甚至几十都有,还要看松茸的分类品级等等,价格再也没有上去过。
采松茸需要走很远的路,特别辛苦。我妈妈现在还会跟我讲,小时候背着我去上山,实在是背不动了,就把我放在一个山腰上,自己再往深山里采松茸。那时候我还好小,也不会爬,我妈妈说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悔,那时都没担心会不会有蛇或者别的野兽来咬我。

等我长大一些,也跟着去采过松茸,但后面读书没有时间,也就慢慢不再去采了。又过了几年,父母年纪大了,他们也不再上山了。
2017年刚开始卖新鲜松茸的时候,哥哥嫂嫂也会偶尔去采,但更多的时候是帮我做一些收购。我们在村里通过合作社来收购村民的松茸,再统一卖给消费者。
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松茸,已经过精心分级,不同的尺寸、新鲜度、颜色、水分等等这些都是分级的标准。我收购松茸只在自己一个村的范围,没有那么大的量,无法做这种精细的分级。所以我们一直做的都是统货,大中小都有,价格是比较居中的。并且只通过一些生态农产品平台和自己的微信客户群来销售。比起市场价,我们的价格可能会稍微偏高一点点。因为我从山上拉到县城来,一趟要走两个半小时,来回就是五个小时,会比其它蹲守在镇子和县里的小商贩成本高。

三、层层分级的松茸产业链
做松茸前,我没有关注过这个产业链。这几年慢慢关注,发现野生菌的销售系统和城市里的分工已经非常接近了,都有很多层级。
采松茸的村民,是这个系统里最低一级的人,他们进山走很远的路去采,不管采多采少,都需要回到村子里,卖给像我这样的收购者。如果没人收,他们就需要拿到村里一个集中的点,然后由这个点再拿到镇上,镇上再拿到县城。到了县城以后,会有不同的去处。每个渠道和不同的老板熟悉,他们会把松茸拿到不同的冻库。这些冻库有些是直接出口的,有些给到餐厅,有些则是对接当地的批发市场,还有些则是给到攀枝花或者昆明等更远一点的批发市场。

还有一些关系更好的,他就能就近进入加工厂。这边有很多野生菌的加工厂,离我们最近的在永仁县,但是规模比较小,离开永仁的话,可以到楚雄的南华县去。在野生菌加工厂里,他们就会一级一级的去给松茸做分级。整个链条很长。
我们的出现,直接缩短了这个漫长的链条。因为我们是直接和农户采购,然后直接给到消费者。我们就能给采摘者一个更好的价格。而且因为大家其实都是村子里的人,什么表哥啊叔叔大伯这种,在我们这种100多人的小村子里面,其实大家都是沾亲带故的。
对我们的做法,以前来收购的小商贩就会很生气,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压低当地的价格。有一度村子里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两派。有一派给我们家,有一派还是给贩子。
在村子里做生意也有优势也有劣势。比如我们没法像贩子那样挑货。采菌子的人会把一天当中采到的所有菌子,除了自己要吃的,都给到我们。不管好的坏的,我们都收,因为你没法不收,都沾亲带故的,没法说我只要你好的不要你坏的。
于是我哥哥就会做分类。松茸适合当做新鲜菌子卖,他就直接给到我,我发货给消费者。这一类松茸我会采取预定的方式,消费者先预定,采到了再发货,这样可以保证新鲜度。另外一些杂菌,如果能做成干货,我这边也可以卖一点。如果既无法当做新鲜菌子卖,也不适合做干货,我哥就需要拉到镇上的采购点去,中间可能能赚几块钱的差价。
四、松茸故事里的虚虚实实
卖了几年松茸,经常有消费者反馈说从我这里买的松茸是最新鲜的。
我也开始研究别人的发货流程等等,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很多电商品牌在宣传里说二三点就上山了,几点几点就拉到昆明发货了,你拿到的东西绝对新鲜。但这个论述至少在我们这里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以我们村为例,农户最早也要三点上山,采松茸的地方往往离村子非常远,回到村子里交货都得到晚上。小商贩又得到镇上交货,镇上又得拉到县城或者是昆明交货。松茸的量比较少,最后拉到昆明去交货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这些松茸必须在昆明集中后,才能做精细化的分级,再去冷库做打冷发货等等。
而且镇上冷库里的松茸不是每天拉走的,但凡量不够,不够他跑一趟县城或昆明,成本不够,他是不会拉走的,都是存在冷库里。必须要量够了,才会到昆明去交货。
在这个存放的过程里面,可能还需要一些保鲜的药物,用来杀虫。野生菌无法保鲜的一大原因是,在菌子慢慢腐坏的过程中,虫卵会孵化出来,所以有人会使用杀虫剂。
又因为松茸是“活”的,所以在存放的过程中会开帽。开帽后,松茸的等级就下降了,因此也有人用药物来抑制这一过程。此外,为了保证水分和新鲜度之类的,也可能会用到一些化学品和药物。

在这些年做松茸和其它野生菌的过程中,我就在反思为什么松茸会成为这么火的一种商品。
很多消费者跟我买了几年松茸以后,问我能不能给他们推荐点其他的野生菌,因为他们不想吃松茸了,已经吃腻了。我只好给他们寄一些很便宜的菌子,没想到他们说怎么这个东西比松茸还好吃。
其实我们自己也觉得松茸并不是最好吃的菌子,但它怎么就被炒成这么贵的一个商品呢,松露鸡枞等等也是这样。
我这几年的经验告诉我,松茸相对其它菌子比较容易保鲜,这就让它适合长途运输。松茸都是在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采,在我很小的时候,既没有冰箱,也没有摩托车可以用来拉到镇上去交,都是小贩走路来收购,再走路去镇上交货,我们在山里等上好几天都不来人。那时候,我爸会拿山里的苔藓把松茸裹好,四五天以后好像也没有很大的变化,还是能卖出去的,只是可能颜色会变黑一点。

松露也是一样,可以像土豆一样随便扔,它也是不容易腐烂的。这类野生菌现在被炒成热门的商品,商家告诉你它具有各种营养价值和高级的味道。我们在开玩笑的时候说,可是大米功效还更好呢,因为你不吃大米就会饿死!松茸作为野生菌的一种真的有商家宣传的种种功效吗,还是说它便于保鲜和运输的特性更适合作为一种商品运作,所以才被推崇?
五、边缘化的人和边缘化的产区
楚雄作为一个松茸产区,这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下降的。虽然松茸的市场似乎越来越大,但产地的价格并没有水涨船高,而且各个产地之间也有竞争关系。
所以我们这边的农户,如果出去工作了,基本上就不会回来采菌子了。留在当地的肯定还会采,但以年轻人为主,因为路实在太远了。我爸爸现在50多岁,他在40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不采了,走不动那么远的山路了。在我们村,现在基本上都是40岁以下的人才会去进山采松茸。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村子里有极个别返乡的人,以前是在城里打工的,到了三四十岁的年纪,城里的工厂不需要他了,他也找不着好的工作,就回来了。但是这些人没有自己的菌窝,因为菌窝都是常年采的人才能找到。他们没有自己的根据地了,就只能去离家比较近的地方,采点牛肝菌或者杂菌之类的,这种不需要菌窝,到处都可以长。

六、菌窝的保育与重生
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松茸的可持续采摘问题。我只能简单介绍以下我看到的情况。
在我家这边,松茸比较容易在那种树特别大,又特别老的,然后是很深的那种深山里才会找到。腐殖土越好的地方,菌丝越厚,有些菌丝可以到一米多深。但这种环境通常是在几个县交界的地区,所以也不太好约束大家保护森林。

我们因为13年做了合作社,对大家是有一些约束的,比如不去砍伐。村民也认识到,保护好森林,森林不仅会出菌子,也有野生药物,还有可以做酵素的野果子。总之,大家出于长远的经济考量,也愿意去保护村子附近的森林。
政府也开始重视松茸产区的可持续保育问题。以我们楚雄南华县为例,1997年,为了保护野生菌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南华县结合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强化对野生菌林下资源的保护,坚持“封山育菌”与“封山育林”相结合。政府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野生菌产业发展的意见》《封山育林育菌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措施和村规民约,明晰权责、引导培训,对野生菌实行持证采摘。
但在其他地区,没有政府出面统一做协调约束,可持续的采摘很难达成。

但我也有一个疑惑:没有政府出面做管理的山林都是公山,所有人都有权利上山采集,一旦明晰权责以后,现在能依靠采菌生活的很多采菌人就无法继续采菌,失去了重要的收入。而且因为这些游离在村庄以外的人群已经远离了土地,但城市又无法接纳他们,他们的生计也会受到影响,不利于巩固脱贫成果。
《末日松茸》一书里面提到世界各地的松茸采集者,似乎也都面临类似的挑战。希望作家阿来在小说《蘑菇圈》最后的悲剧,不要发生在我们这片山林。
〇本文根据2021年6月16日康丽在由食通社组织的《末日松茸》读书会第二次线上共读中的发言整理而成。
“康丽的讲述,串起了一颗松茸背后人与时代的变迁。如何形容一颗松茸也变成复杂的事情——在流行的营销话术里,它是极品珍馐;但对产地的当地人来说,它甚至不是味道最好的菌子;职业松茸收购者视它为现金流;对当地采摘者来说,松茸则象征着他们与赖以生存的森林之间的平衡;松茸是处在深山的村民与市场经济的交点,但也可以成为支撑村庄内部力量生长的资源。
如同《末日松茸》一书展示的那样,松茸凝结着不同生命互相缠绕的经历,启发我们去思考食物背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
——李舒萌《末日松茸》读书会领读人
活动预告
2021年6月30日(三),20:00-21:30《末日松茸》第四次线上共读
【内容】:《末日松茸》“第四部分 事物之间”及全书
【领读嘉宾】李舒萌(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分享嘉宾】覃延佳(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平台】腾讯会议 ID:807 555 878;点击链接入会:https://douc.cc/29YuMo
▼
扫码回听往期共读

食通社是一个可持续食物与农业的知识、信息和写作社区,由一群长期从事农业和食物实践及研究的伙伴们共同发起和管理。我们相信,让消费者了解食物的来源,为生态农业从业者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和社会环境,我们的食物体系才能做到健康、美味、可持续。
微博/豆瓣/知乎:食通社
微信公众号:foodthinkchina微信小号:foodthinkcn
官方网站:www.foodthink.cn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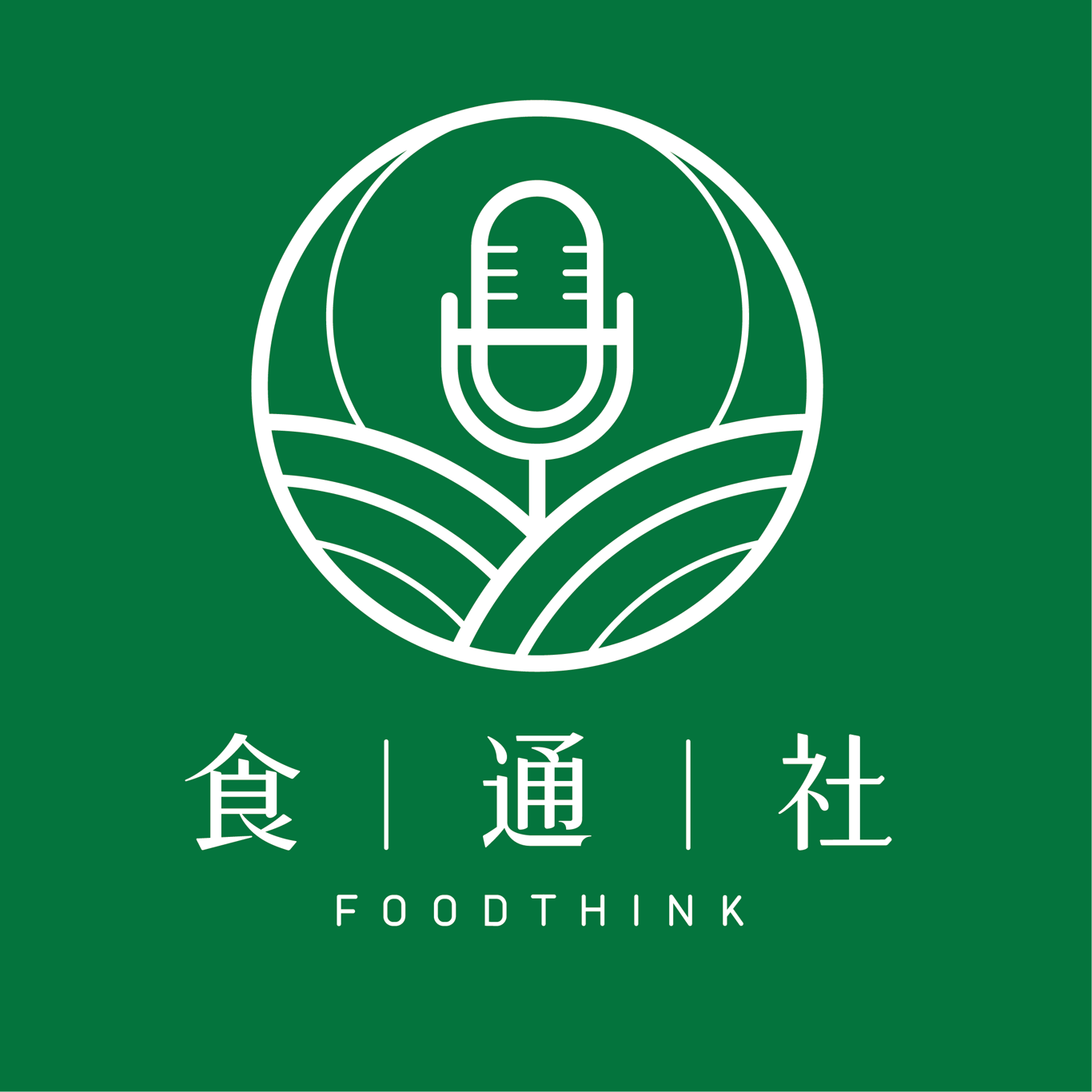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